从“预思”死亡,到“预演”死亡
哲学家朱锐在被宣布仅剩数十天的生命,每天都在体验身体的疼痛与功能丧失之际,与年轻人进行了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他说:“对话是最好的告别方式。”这些谈话,加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的部分内容,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辑成一个小小的集子问世,名为《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4月第1版)。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书封
我读之再三,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对一个哲学概念的不同看法。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将人类称为“面向死亡的存在”。在他看来,既然人类能够意识到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那么真实地生活就意味着直面这一事实。这就是他所谓的“向死而在(生)”(Being-towards-Death),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具有根本地位。
朱锐先生说,他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他的理由是,当死作为一种确定性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何谈时间的未来与现在的筹划?一旦死亡直逼而来,在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身体结构和心智结构已经被完全改变(《哲学家的最后一课》,第62-62页)。
这是一个被预先宣判将要死去的哲学家的切身体验。因为他面对着某种死的悖论:“我的心智很成熟,完全健康,但是身体已经彻底失控,人格也不再有同一性。”(第48页)可以说是,精神未死,但身体将亡。到最后,“一口水,一碗汤,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侈”(第52页),人生最大的快乐,是走到医院对面那条街上的饭馆,进去点餐,坐下来吃饭(第51页)。
朱先生的意思是说,面对死,只有保持自由的筹划,才能叫做“向死而在”。而存在主义所说的“向死”是一个健康的人用一种思想实验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和一个癌症患者知道自己只有半年甚至只有半个月的生存期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向死而在是真切地知道,在一个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时间维度内,生命即将结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必然性,是一种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宇宙的残酷。”(第64页)
可以这样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在是存在意义上的,朱锐先生所说的向死而在是身体意义上的。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927)中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简单:存在即时间,而时间是有限的。对于人类来说,时间的终结就是死亡。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就必须不断地将我们的生命投射到死亡的视野中。只有在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并努力在死亡的事实中寻找意义时,我们才能建立起真实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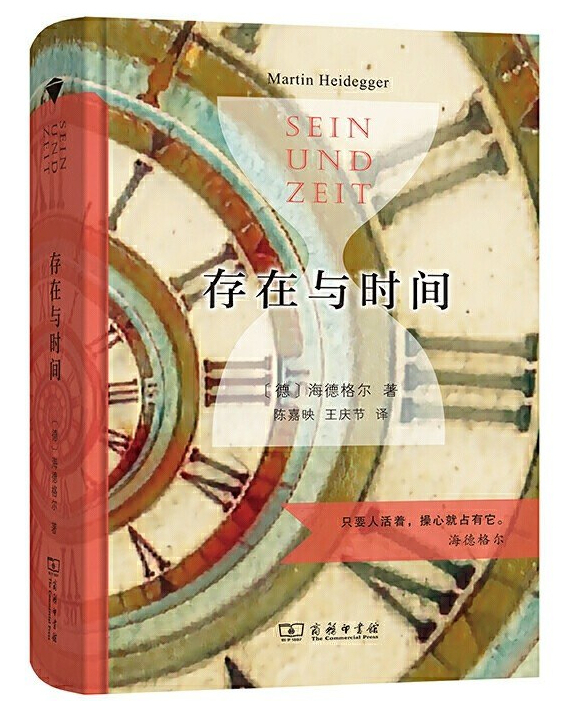
《存在与时间》书封
这让我们想起那句古老的格言:“哲学就是学会如何面对死亡。”(To philosophize is to learn to die.)这个观点源自16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而蒙田又是引用了西塞罗(Cicero)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蒙田曾表示,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想象中常常想到死亡,甚至死亡就近在嘴边——在吃的食物、喝的饮料中,都带着死亡的意识。蒙田写道:
“为了从根本上剥夺死亡对我们的最大优势,让我们采取一种与常规完全相反的方法。让我们消解死亡的陌生与新奇感,让我们与死亡建立亲密的关系,时常将其置于我们的思绪之中。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死亡的不同面貌呈现在我们的想象中;在马失前蹄时,在瓦片掉落时,甚至在针刺伤时,让我们立刻反思,并对自己说:‘好吧,如果那就是死亡呢?’然后,让我们鼓励自己,增强自己的勇气。”
对于那些稍微喝多了一点的人或是不小心撞到树上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能听起来不无阴郁。但其实并非如此。蒙田说:“无论在欢乐和宴飨中,我们都要用脆弱的生命状态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让自己因欢乐而过于忘我,忘记去反思和考量我们欢乐的每一刻是如何通向死亡,又有多少潜在的危险威胁着它。”
他最终以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来总结他的思考:“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思自由;学会如何面对死亡的人,便学会了不再为奴。”这一观点振聋发聩:奴役的本质是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对消亡的恐怖,让我们永远处于束缚之中。
由此,死亡构成了我们塑造和构建自我认知的基准。在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的思考与这些哲人是一致的。例如,他多次提到,他曾进行“死亡练习”,这比蒙田更进了一步,不仅是“预思”死亡,甚至是“预演”死亡,为的是摆脱对死亡的恐惧(第10-16页,第19页)。2024年春,在授课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对学生说“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导言第16页),要用理性和知识,实现从恐惧到不恐惧(第5页),这也即是“追求灵魂的自由”(第22页)。
以“本真”的方式无畏地存在
海德格尔讨论死亡时,的确有忽略身体的趋向,对他而言,向死而在指的是人类自知死亡不可避免,并以一种本真(authentic)的意识来面对这一事实的存在状态。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关于肉身的终结,更关乎人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如何理解存在、如何作出选择。
他曾在德国南部黑森林地区盖起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作为他常年的工作间。他在那里感受到四季的变换以及山野的沉重与树木的生长。“在隆冬的夜里,当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咆哮着铺天盖地而来时,”海德格尔写道,“接踵而至的就是哲学的美妙时光”。
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哲学工作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它属于农夫的劳作,因此他的思想应该坚硬、直截而又沉重,就如同那荒凉的山上世界。海德格尔常常孤身一人在此思考,但他并不觉得孤单。相反他相信这种孤独具有最本源的力量,它使人的此在(Dasein)走向了万物本性的近处。
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海德格尔开始写作一部后来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哲学著作,那就是前文所说的有着里程碑般题目的《存在与时间》。这部长达1500页的哲学著作内容艰深,可是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表达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寻找和找到的生命感觉。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去认识我们究竟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在海德格尔看来并非如同一个物体那样存在着,他不是简单地在那里,而是有一个“此在”,此在在世烦忙于世,烦神于人,合烦忙与烦神,烦(Sorge)被称作此在存在的整体性(这里用陈嘉映先生的译法)。
此在存在于出生和死亡之间;当此在还活着,还没有完结,它如何得以达到整体性呢?这里必须引入死亡。“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死亡不是一个对生存漠不相关的终点。死亡之为终点把生命的弦绷紧了。生命正是由于充满紧迫感造成的张力而成其为生命的。这样在生存意义上领会死亡被称为“向死存在”。“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
这个此在在海德格尔那里绝非避难的天堂,正相反,那是一笔“债务”。死亡等待在生命的尽头,不只是他人的死亡,而且是你我的。认识此在的这一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其中包含着生命的本真。但是畏惧(Angst)等待在这种本真之中,并非面对确定之物的畏惧,而是作为人的深不可测的本性的畏惧。在经验这种畏惧之前逃避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尔了解这种逃避的许多方式:逃入某种烦,也即逃入策划、盘算和期待之中;逃入消遣,逃入到那些所谓的“常人”(Das Man)之中,进入其中没有人是他自己的舆论,消失在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之中。
所有这些逃避手段在海德格尔看来最终都导致人将自我掩蔽起来,僵化地生活而且割断生活和自我的联系。如果人们能够承担起这个世界的重负,如果人们有勇气忍受面对空虚时的恐惧,如果人们以加倍的镇定坚守在这种危险的此在之中,那么人们将会以“本真”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存在。
死亡的四个正式标准
海德格尔区分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死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不同类型的存在者以不同的方式结束。
仅仅作为生物的存在体,在某个事件或过程使其身体无法继续维持有机功能时就终结了,海德格尔将这种终结称为“亡故”(Verenden,德语意为“结束”或“完成”)。这是任何生物体的终结,是纯粹的生理死亡,适用于“仅仅活着的东西”(包括非此在的生命体,如动物)。对于人而言,“亡故”即临床意义上的死亡,它是一个经验性的事件,而海德格尔恰恰指出,“死不是一个事件”。

海德格尔
为此,海德格尔还进一步区分了“人的非本真的离去”(即“辞世”,Ableben)与“真正意义上的死亡”(Tod)。辞世是一个“降临在某人身上的事件”,它使一个人丧失了扮演社会和法律角色、拥有体验和追求目标的能力,却不一定伴随着存在性的领悟或承担。而“真正的死亡”则不是降临在我们作为“人”(person)的身份上,而是降临在我们作为“此在”的存在上。它更应视为“生存性的死亡”(existential death)——死亡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个事件,它揭示了存在的边界。
所以,海德格尔的死亡概念并不是死亡之后的状态,而是此在在生之中所面对的极限可能性。为了把这一切贯穿起来,海德格尔赋予“生存性的死亡”以本体论上的重要性,因为它揭示了人类存在可能性的根本特征。如果“生存性死亡”始终作为对“我是谁”的一种威胁潜伏着,那么“我是谁”就永远不可能以一种稳定的方式来描述。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就在于开放性、不确定性,是一个始终面向未来的“可以是”的存在。死亡之为“不可能的可能性”,揭示的正是人永远无法被某种既定身份或特性完全界定——因为人始终处在可能性与未完成之中。
如果死亡是我们用来塑造自我身份的一个根本参照,是此在所有可能性中最根本、最个人化的“可能性”,它就不能被与其他形式的终结或“耗尽”相提并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仔细衡量一下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在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观念当中,死亡有四个相当正式的标准:非关系性、确定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可超越性。
首先,死亡是非关系性的,这意味着站在死亡的面前,人已然切断了与他人的一切关系。没有人能替你死,死亡也无法通过他人的死亡来体验,而只能通过我与自身死亡的直接关联来体验。
其次,死亡是确定的。尽管人可能逃避或否认这一事实,但没有人会怀疑,生命最终会以死亡作为终结。正如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如果允许自杀,那任何事情就都可以允许了。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应该允许,那自杀肯定有份。”
第三,死亡又是不确定的。虽然说死亡本身是确定的,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它何时、如何降临。大多数人希望拥有长久且充实的生命,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死神敲门的时间和方式。这也就是蒙田所讲到的:“死亡等待我们的地方是无法预知的;让我们随时准备面对它。”
最后,死亡不可超越,这意味着死亡极其重要,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超越它。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死亡是‘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悖论性论断背后的思想。死亡是我存在的潜能所要衡量的极限。它是那种根本的无力感,正是它让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完全破碎。
在《存在与时间》导言的结尾,海德格尔写道:“高于现实的是可能性。”《存在与时间》不是一部悲观的著作,而是一首对“可能性”的长篇赞歌,其最高表达形式便是向死而在。海德格尔区分了“预期”(Vorlaufen)和“等待”(Erwarten)。他的主张是,如果等待死亡,仍然包含过多的现实性,因为死亡将是可能性的实现。这样的哲学会陷入病态的阴郁之中;相反,预期并非消极地等待死亡,而是把死亡作为自由行动的条件,以此来动员生命的有限性。
这告诉我们:自由并非缺乏必要性,尤其是死亡的必要性。相反,自由在于对自己的有限性——即死亡的必要性——的肯定。只有在向死而在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死亡作为“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观念背后,隐藏着对自我有限性的接受,而这种接受正是肯定自己生命的基础。
因此,向死而在并非病态的哲学思考。海德格尔的观点是,向死而在将此在从对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沉浸中拉出来,使其回归自我。只有在向死而在的过程中,我才会充满激情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由。
当“常人”面对死亡所带来的畏惧时,它选择转移注意力,把被子拉上头,把死亡视为某种“终将到来、但尚未到来”的遥远现实,从而逃避其所带来的不安。而本真的此在(authentic Dasein)则踢开那层安全的被褥,直面床底下的怪物,也就是那不确定的、令人麻痹的未来。它不再依赖于已经坍塌的世界,而是孤身一人、裸露地面对死亡,并在这崩塌之中重新认清自己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并得以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我理解,这也就是朱锐先生所说的“从回避死亡到庆祝死亡”(第 118页)。
死亡是生生不息的来源
海德格尔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起码有一点是可以商榷的。海德格尔认为,唯一真实的死亡是自己的死亡。然而,死亡向来是通过他人的死亡而进入我们的世界的,无论是像父母、伴侣或孩子这样的亲近之人,还是远在他乡的陌生人,如远方饥荒或战争的受害者。与死亡的关系,首先并非是我对自己死期的恐惧,而是我通过悲伤和哀悼体验到的被撕裂的感受。
人类的死亡意识不仅涉及自身的终结,还在于我们如何通过他人的死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朱锐说:“面对家人的离世,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死亡练习’。”(第122页)同样地,我们现在向朱锐先生学习如何死亡,也是在进行“死亡练习”。

汉娜·阿伦特
谈到死亡,我觉得需要以海德格尔的弟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作为对这位老师的补充。《存在与时间》带着海德格尔进入了哲学世界全新的领域之中,而阿伦特参与了海德格尔的新的探索。人是否得到了向往的生活,也就是说,那生活是否真实,在海德格尔看来取决于个人。他必须寻找到一种与自身的不同以往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与同类、与“常人”及其“闲话”(Gerede)自觉的离弃之中。
在阿伦特看来正相反,人的入世意味着他/她与别人分享世界,因此他/她的行为总是针对自己的同类并且必须开放。她因此不同意海德格尔对于“常人”的摒弃,以及他关于人只有单独地、在摒弃了他人之后才能寻找到自我的观念;而是认为,人在行动中发挥了其最大能力,那是一种天赋,它开创某种全新的东西,使一个难以估量其结果的过程运转起来。
阿伦特用“创生”(natality)一词来概括这种能力。她以此反对曲解向死而在思想的哲学家,在他们看来,生活如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某个寓言故事里的老鼠,它从广阔的田野里跑进越来越窄的房子,直到最后进入一个房间,一只猫正等在墙角里——生活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如此方为认识生活的途径。
作为思想家(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性格取向),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十分关注事情的开端和结局。海德格尔醉心于开端的力量和光辉,但却将其作为一种遥远的和冷静的爆发而加以体验,一如上帝的创世或希腊人的创世哲学。他的思想被吸引到个人生存的短暂和环绕其外的无尽的虚无中,不过,尽管如此,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端赖于每个人自己去建立。
对结局的熟悉阿伦特体会很早;她7岁的时候,父亲和祖父就双双身故。对死亡的恐惧始终伴随她的童年,然而这些恐惧在她成熟以后消失了,或说得到了她的控制,她随即把思想集中在创生上:开端的反复重演,新生的力量,具有改造能力的思想,她醉心于这些东西如何被植入世界的持续之中。甚至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这部记叙了欧洲文明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灾难性崩溃的力作的结尾,她也不忘乐观地歌颂重新开始的潜力:“开始是人类的最高能力”,接下来她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肇其始,创其人。”她作结曰:“这个开始,被所有的新生所保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的起源》书封
阿伦特的思想核心是,开始,既史无前例又无法预知,是人类自发、自主的源泉。同样核心的是多样化:每个人生而进入的世界都是与他人分享的世界。当我们到达这个世界之时它已经在移动;只有通过加入舞蹈我们才会变成我们自身。
在阿伦特看来,每一次实在发生的行为不是对死亡的前瞻而是对出生的回顾。如果死亡是最大的平均主义者,那么在她看来出生就是那个奠定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的事件。也只有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新的东西。对此阿伦特写道:“先天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的一个新人,一个开始,一个新生儿,因此人们可以掌握主动,敢为天下先,开创新事业……新的开始不断处于与在统计学上可以把握的可能性相矛盾的状态中,它永远是不断的不确定,因此,当我们在活生生的经验中与它相遇时……它永远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奇迹。”
所以,阿伦特才会以一句名言传世:爱这个世界。
这令我想到,朱锐先生强调,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肯定,是重生(第29页)。死亡是生生不息的来源(第27页)。他说:“或许有一天,人们面对死亡,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广义上的‘重生’,而不再是恐惧与幽暗。”(第125页)就让我以这个愿望结束我这篇小小的对死亡的感受之作:我们向死而在,但爱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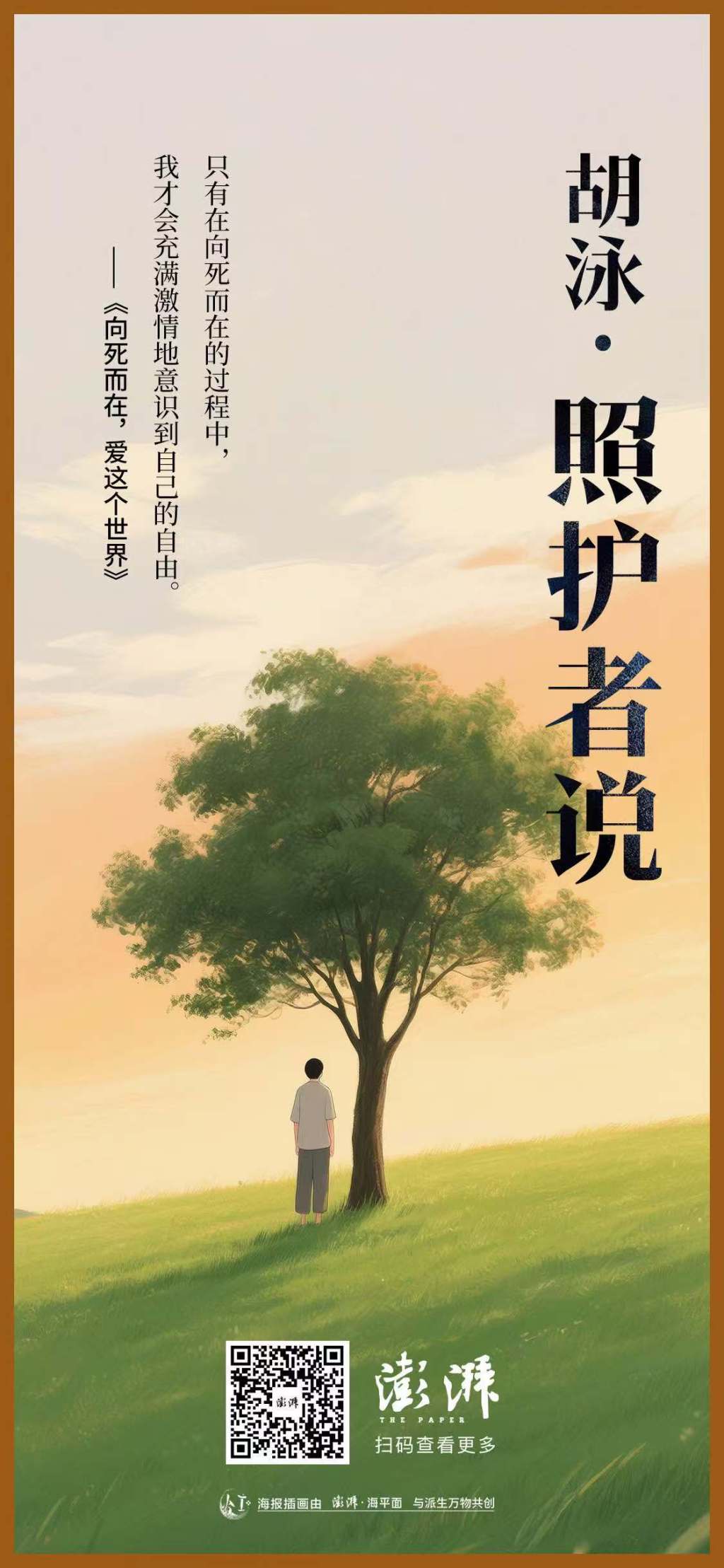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照护者说|胡泳:向死而在,爱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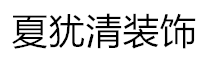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0
京ICP备2025104030号-10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